近来,中澳关系仍在不断探底。
9月15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污蔑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馆及其官员“从事渗透活动”,将中国驻澳使领馆正常履职行为政治化、污名化;12日,澳大利亚警察于今年6月26日秘密搜查四名中国记者一事曝光;同一时间,两位从事澳研的中国学者陈弘和李建军被澳大利亚政府无端撤销了签证;再之前,两名澳大利亚记者(他们也是澳媒在华雇佣的最后两名记者)离开中国,澳媒又借机大炒了一阵“震惊和愤慨”。
8月28日,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领导的政府宣布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外交关系法案,要求所有州政府与外国签订协议前,必须事先得到联邦外交部长同意。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一带一路”备忘录、澳大利亚各大学建立的“孔子学院”,乃至与中国签订的一切协议,都成了该法案的标靶。
看着澳大利亚在“作死”的道上一路狂奔,众多有识之士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连篇累牍地撰文喊话,试图劝说堪培拉“悬崖勒马”。不论是出于利害关系而发声、还是真正的知华友华派,核心观点都是一致的:
现在的中澳关系太糟了,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最急的是澳大利亚农民
8月19日,澳大利亚全国农民联合会呼吁莫里森政府“培育”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联合会首席执行官托尼·马哈尔认为政府和工业界需要“尽我们所能保持我们两国之间的对话的开放性”;反对党工党的农业发言人乔尔·菲茨吉本指责莫里森对两国关系恶化负有“责任”,“中国是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也是我们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很愤怒,将惩罚我们”。

企业界纷纷“示警”。
有商业背景的智库“中国事务”(China Matters)警告称,如果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澳大利亚可能会受到“连带损害”;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前董事会成员约翰·爱德华兹在为罗伊研究所撰写的文章中称,“迄今为止,澳大利亚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并没有表现出它日益需要的聪明才智……拒绝在中美贸易和技术竞争中站队,是澳大利亚宣布的政策。它被明智地采纳了——但没有被巧妙地实施”;澳大利亚最知名的全球高管之一、前美国陶氏化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安德鲁·利弗里斯警告澳大利亚政府,不要混淆经济和安全关系,以免在中国崛起的“新现实”面前犯错误。
学界大声疾呼
“不要在澳大利亚的安全问题上玩弄政治”,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AIIA)研究员梅丽莎·康利·泰勒写道,“我担心,一种危险的民粹主义进入了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辩论……要驾驭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基于谈判的心态,而不是简单解决方案的绝对主义。”
“这已成为外交政策圈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作为一个在经济上严重依赖崛起中的中国、但仍与美国保持着强大安全联盟的中等大国,澳大利亚在处理两国关系时是否算错了算盘?”英国《卫报》写道。
该报采访了四位相关领域的专家,其中三位对堪培拉的做法持批评态度:
澳大利亚前外长、新南威尔士州前州长、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鲍勃·卡尔表示,“从任何看似对抗的事情上后退一步,等待一个更适合合作的气氛寻求发展,这是在澳中问题上唯一的建议”;
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埃琳娜·柯林森说,“中国是一个不会消失的现实”,澳大利亚应该“努力保持联络渠道的开放,并尽可能集中精力缓和紧张局势……寻求对话和妥协不应被视为软弱”;
曾任驻华记者的《悉尼先驱晨报》资深编辑哈米什·麦克唐纳称,堪培拉“应该听取更好的建议,避免犯一些愚蠢的错误”,比如马尔科姆·特恩布尔的“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的言论,以及莫里森的挑衅性行为——后者要求如“武器核查员般的权力”,到武汉对新冠病毒源头进行独立调查。

视频截图
连一向对中国没有好话的澳大利亚主流媒体,都出现了“求三思”的声音。
中国澳大利亚商会华西总经理习克礼在《悉尼先驱晨报》发表文章,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必须调整其措辞和做法,不要浪费在华战略机遇”;《澳大利亚人报》刊文《我们和中国的关系需要帮助,否则就太迟了》,称“在堪培拉的部分官僚和政治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危险的情绪。除此之外,这些危险现在也延伸到了我们那些制造观点的精英们身上”;文章称,假定“中国是敌人”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这是一条走向毁灭的道路,但它也有拥护者”,“如果今天的恶性循环再持续三到四年,这个国家将会损失惨重”。
该文作者、《澳大利亚人报》前主编保罗·凯利难得地(尽管也是不情愿地)承认,所谓的“中国干预”完全是子虚乌有:“在这个灰色地带,干涉和影响之间可能只有一线之隔……本世纪初,澳大利亚驻美大使迈克尔·索利在美国国会组织了‘澳大利亚之友’(Friends of Australia)组织,向美国政治体系施压,要求其与澳大利亚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今天,澳大利亚议会却根本不可能容下‘中国之友’。任何这样的影响都会不可避免地被视为干涉。”
来自政界的声音也足够重量级。
前外交官、曾在陆克文和吉拉德政府担任幕僚长的艾伦·贝姆表示,“目前,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绝对已经陷入僵局”,“政府应该认真听取外交人士的意见,切实制定正确的对华外交政策和战略规划”;前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芮捷锐(Geoff Raby)称,“现实主义是澳大利亚与中国接触的关键”;陆克文在美国《外交事务》上撰文,借回顾一战告诫警惕“亚洲的八月炮火”;另一位前总理约翰·霍华德则呼吁澳大利亚应“继续努力保持双边关系和谐稳定。重要的是我们不要放弃一个务实的对华关系”。
情报机构和将军正主导澳洲外交
这些呼吁的来源不可谓不广、声音不可谓不有力,在其他国家很少能听到如此多珍惜、改善双边关系的呼声,可以说,多年来培育、巩固中澳友谊的努力并没有白费。遗憾的是,这些理智的声音在澳大利亚舆论场并不占主流,它们对澳大利亚决策者的影响力更是非常有限。有识之士的苦口婆心,对堪培拉来说犹如对牛弹琴。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市场,该国的经济支柱——矿业和农业都严重依赖中国,这些行业的从业者也是中澳关系发展的最大受益者。然而,他们虽然也是澳大利亚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但对该国的对外战略却缺乏话语权。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金融和政治精英,他们几乎一边倒地依赖美国,因此在面临“站队”时,澳大利亚宁可牺牲农矿业的利益,也要追随美国路线,无条件地与中国对抗。
这与其说是澳大利亚精英的主观判断,毋宁说是没有选择的选择。自二战以来,澳大利亚在投资、军事和情报方面一直严重依赖美国,无法承受与美国“脱钩”的代价。莫里森今年7月在宣布扩军计划时就强调了对“与美国日益紧密的联盟关系”的承诺,称这“是我们国防政策的基础”。他宣称:“我们与美国享有的安全保证、情报共享和技术产业合作对我们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而且将继续如此。”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资料图)
如果是正常国家,决策层势必要平衡经济与安全利益,但澳大利亚做不到这一点。《澳大利亚人报》的保罗·凯利就写道:
“澳大利亚政府需要确保情报和安全机构不主导双边关系。一位政策资深人士告诉我,‘这些机构现在的影响力超过了冷战时期’。”
专栏作家罗斯·吉廷斯也在《悉尼先驱晨报》上写道:
“请各位将军注意:中国是我们不可避免的经济命运。在澳大利亚的历史上曾有过这样的时候:人们看着这个国家的经济专家,想知道他们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今天,情况正好相反:关心我们经济未来的人们正在想,国防和外交事务专家是否知道他们正在玩什么游戏?”
对任何国家来说,由情报机构和将军主导对外关系都不是什么好事,但澳大利亚,就像他们忠心追随的美国一样,就是这么充满着“昭和气息”。这两个领域也是澳大利亚最亲美的。
自一战以来,澳大利亚的国防就一直仰赖美国,1951年《澳新美安全条约》签署后,美澳军事同盟关系更是紧密异常,澳大利亚军队参加了美国的每一次重大军事干预,从朝鲜一直打到伊拉克;上一届工党政府积极支持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战略,并同意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北方城市达尔文派驻美国海军陆战队。如今,尽管面临着新冠疫情和严重的经济困局,堪培拉仍豪掷2700亿澳元扩军,莫里森还在接受保罗·凯利采访时夸耀,他的政府已经“豪越”(crashed through)了将军费提升到GDP 2%的目标。
情报领域的美国因素更是浓墨重彩。身为“五眼联盟”的一员,澳大利亚情报机构深度参与了美国在全球的间谍活动,从窃听全球电子通信到暗杀卡西姆·苏莱曼尼,澳大利亚人无一缺席。在反华领域存在感极强的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日常工作就离不开美国同行的“协助”。这也是为什么澳大利亚在抵制华为时格外卖力、美国也对此异常上心。
除了军事和情报,影响澳大利亚决策的其他重要领域也笼罩在美国的影子之下。澳大利亚的传媒主要掌握在两个机构——第九频道(Channel Nine,旗下包括《世纪报》、《悉尼先驱晨报》和《澳大利亚金融评论》)和鲁珀特·默多克集团(《澳大利亚人报》、《悉尼先驱太阳报》和《每日邮报》)手上,后者虽然生于墨尔本,但主要舞台却是在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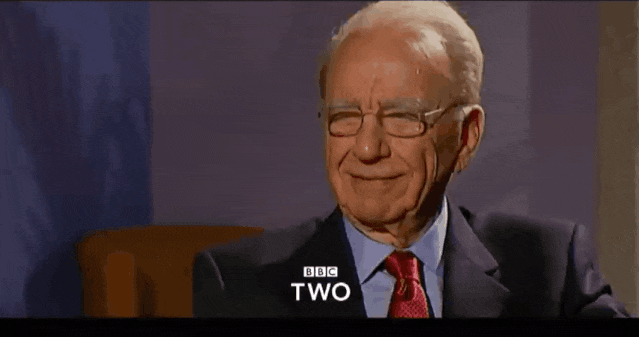
学界的美国干预也是树大根深。2007年,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政府的资助下,悉尼大学成立了“美国研究中心”,目的是消除对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反对声音。其他许多大学也纷纷开设各类“智库”和“对话”,与澳大利亚和美国军事与情报部门的代表密切合作。例如2016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就在墨尔本大学成立了一个由澳大利亚政府资助的新研究中心,以开发军事技术。截至2018年,已有32所澳大利亚大学成为该国国防部于2014年启动的“国防科学伙伴计划”的合作伙伴。
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是美国资本的无形之手。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小亚瑟·库尔豪斯最近的一段表态对此说得非常明白:7月下旬,也就是蓬佩奥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讲后不久,这位大使就在悉尼大学的美国研究中心表示“美国的投资对澳大利亚未来的繁荣至关重要”,警告不要试图将“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分开,并补充说:“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库尔豪斯试图将澳中关系和澳美关系进行对比,声称中国对澳大利亚进行了经济恐吓,但“澳大利亚永远不会看到美国大使威胁要停止与澳大利亚的贸易和投资”,尽管此言听上去更像是一种威胁。
美国大使称赞一份由澳大利亚美国商会委托的报告“非凡”和“辉煌”,该报告得出结论称,美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重要性远远超过中国,美国已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单一外国投资者,截至2019年,美国投资总额为9840亿美元,超过所有外国对澳投资的四分之一;澳大利亚对美国的出口和美国在澳大利亚投资产生的收入每年贡献了1310亿美元,占澳大利亚年经济增长的7%。
该报告还强调,早在新冠疫情之前,澳大利亚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公共和私人债务就已经高达1.1万亿美元。“为了复苏,澳大利亚知道它必须、而且将能够进入美国资本市场,”报告称,这是世界上“最有深度的”资本市场。
对外转移矛盾成为美澳共同选择
陆克文的经历表明,如果澳大利亚政治人物试图冒天下之大不韪、推行平衡外交,他们会遭遇怎样的命运。
2010年6月24日,陆克文在一场工党的党内政变中被推翻,其副手朱莉娅·吉拉德接替了他的位置。公开的报道中似乎一切正常,但维基解密当年12月公布的美国秘密外交电报却显示,美国驻堪培拉大使馆才是政权更迭的关键所在。
包括澳大利亚参议员马克·阿尔比布和大卫·伊恩·菲尼,以及澳大利亚工会主席保罗·豪斯在内的党内政变关键策划者,一直在秘密地定期向美国大使馆提供澳大利亚政府内部讨论和领导层内部分歧的最新情况。维基解密的文件显示,华盛顿和澳大利亚政党、工会等组织的关系盘根错杂,谁将担任堪培拉的高级职位,决定权并不全在澳大利亚手中。
陆克文完全遵循二战后澳大利亚工党的传统路线,致力于维护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但在美国人看来,他还是太亲华了。陆克文曾提议建立一个亚太共同体,试图调解美国和中国之间不断升级的战略竞争,并反对由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组成的针对中国的四方军事同盟。
陆克文的下台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澳大利亚的统治精英们再也没有任何含糊其辞的余地,无论哪个政党执政,它都必须无条件地支持美中冲突,无论失去其在中国的庞大市场会带来什么后果。

成为总理后,吉拉德的第一次公开露面便是会见美国大使。她很快与奥巴马通了电话。作为“奖赏”,2011年11月,奥巴马在澳大利亚国会,而不是白宫,宣布了他的“重返亚洲”战略。这次访问期间,吉拉德和奥巴马签署了一项协议,允许美军驻扎在达尔文市,并允许美国在澳大利亚使用更多的军事基地。
2013年,工党国防部长斯蒂芬·史密斯提出的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将“印太”明确列为澳大利亚的战略重心。这一主张经历了四个总理(一个工党、三个联盟党)和六个国防部长,一直延续至今。2018年,当特恩布尔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备忘录后,他被莫里森所取代。此前,奥巴马曾亲自指责特恩布尔未事先通知华盛顿,就让一家中国企业获得了达尔文商港99年的租赁权。
“2018年8月,当特恩布尔将华为排除在5G建设之外时,他让全世界知道,他像一个忠实的小学生一样给唐纳德·特朗普打了电话。”澳大利亚前外长鲍勃·卡尔写道,“2020年,当我们要求对新冠源头进行调查时,我们的外交部长突然在我们的总理与美国总统通话仅仅几天后发出威胁,要对中国进行‘武器核查’。”
2020年7月28日,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玛丽丝·佩恩和国防部长琳达·雷诺兹不顾新冠疫情访问美国,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澳大利亚-美国部长级磋商(AUSMIN)。双方在会后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其中原样复述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所有煽动性指控,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胁迫性和破坏稳定的行动”到“对其他国家的恶意干涉”。会议还宣布在达尔文市建设一个大型美军燃料储备,并“重申”两国致力于进一步结成旨在包围中国的四方军事同盟。
会议前夕的7月23日,莫里森致信联合国,宣称中国在南海的相关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中国的海洋权益声索是“无效的”。这标志着澳大利亚正式放弃了在中国南海问题上的中立政策。
“防务和安全机构、联盟党后座议员、美国资助的智库以及默多克主导的媒体组成了一个协同战线,攻击中国”,南澳大利亚大学教授贾斯汀·奥康纳在《珍珠与刺激》(Pearls and Irritations)网站上写道。面对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对外转移矛盾成为美澳统治阶级的共同选择。
“在充满不确定性和多重全球紧急事态的当下,还有什么比对中国开战更好的主意呢?”奥康纳问道。
但这真的是一个好主意吗?奥康纳知道答案,澳大利亚政客也知道答案,只是他们不敢揭晓这个答案。


